安全检查是强化安全监管,治理安全隐患,防范各类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。安全检查的力度和效果,直接关系到企业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,直接影响到地方的发展与稳定。当前,安全生产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,安全检查必须进一步充实内涵,完善措施,提升实效,充分发挥宣传引导、查纠整改、追责警示等功能。
宣传要到位。要充分利用安全检查时机,深入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有关新政策、新文件、新标准等,确保安全生产的新制度、新规定、新要求及时走进企业,为企业所理解,为企业所掌握,为企业所运用,落地生根,落地生效。
引导要到位。要深入宣讲科学发展观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、调整产业结构、节能减排等科学发展理念,引导企业着眼长远,加大投入,加快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工艺,加快推进标准化管理,强基固本,提速增效。
查纠要到位。要突出检查重点,重点检查事故易发多发领域、行业和环节;要细化检查内容,不仅查人员、查设备、查仓储,还要查台帐、查资料、查管理;要完善检查方式,在抓好常规安全检查的基础上,适度采取专家检查、随机抽查、暗访等方式,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。
整改要到位。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,要做好登记,强化跟踪,督促企业及时采取措施,逐条整改到位;对一时较难解决的事故隐患,要督促企业制定专项整改方案,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到位”;要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制度规定,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层级、每个岗位、每个员工,严禁违章指挥、违规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“三违”行为。
追责要到位。对安全隐患敷衍应付、整改不力的,要坚持原则,从严要求,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;对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单位,要敢抓敢管,真抓真管,该停产整顿的要坚决停产整顿,该关闭取缔的要坚决关闭取缔。对拒不执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指令的,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。
警示要到位。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和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,让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,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严肃性,切实把安全生产摆到首要位置,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、安全与效益、安全与稳定的关系,时时想安全,事事抓安全,处处重安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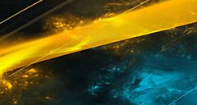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列表